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作者陈玮。视频采访:澎湃新闻记者 谷晓丹(03:03)
【编者按】
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已出炉。观察和研读最新评选出的10篇年度论文,我们对近一年来上海社科学者的研究方向会有一个概括性认知,既有“全球供应链重构、科技创新机制、全媒体时代、无形经济、信息保护、代际共育”等当下时代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,也有“历史书写、政党与国家、唯物史观、中国美学”等关系中国学术研究的机理问题。
“年度论文”评选活动由上海社联2013年组织发起,至今已连续开展12年。年度论文评选无需作者自行申报,而是依托各学科权威专家、学术期刊主编、资深学术编辑等专业力量,开展多轮遴选评审。
澎湃新闻记者对话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获奖者,听学者讲述数字时代学术研究的坚守和改变,新文科建设如何创新,以及学者如何研究真问题,回应时代之问。
中国经济体制的特色在于拥有不同所有制混合的产业体系,因此,能兼容国企与民企两种制度环境。那么,两种制度环境如何发挥各自优势,更好孕育与支持技术创新?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陈玮认为,国企、民企分别在“长周期技术”产业及“短周期技术”产业创新方面各具优势。
如何化解不同制度环境的不完美?在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《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技术创新——以技术周期为视角的考察》(原载于《探索与争鸣》2024年第7期,作者陈玮、耿曙)中,陈玮等作者指出,中国产业体系中,国企与民企是互补的,双方基于各自优势,展开多样的产业布局,追求不同领域的技术创新,从而展现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制度优势,为广大后发展国家提供创新发展的路径借鉴。
2025年1月,澎湃新闻就论文中谈到的相关问题专访陈玮,她认为,钢铁业、造船业和发动机制造等属于“长周期技术”产业,新技术出现缓慢,旧技术退出也缓慢。半导体和信息技术等则为“短周期技术”产业,技术更新迭代快。然而,没有一种制度环境是完美的。国企所处的制度环境,使得国企决策往往滞后于市场变化,存在组织与网络僵化的问题。民企所处的制度环境,则使得民企由于融资不足,难以长期专注于溢出效应更大的创新活动。
国企与民企为技术创新带来不同的制度优势
澎湃新闻:从培育技术创新角度看,当前中国国企与民企所处的制度环境有何不同?
陈玮:中国国企与民企所处的制度环境,在治理模式、金融关系、劳资关系、协作网络等方面均有所不同,且这种差异是系统性的。两者的核心差别体现在,企业在环境中的决策是遵循“非市场调节”还是“市场调节”。比如,国企所处的制度环境使其以“非市场”逻辑进行决策,民企则主要遵循“市场”逻辑。
因此,国企需承担国家战略产业发展任务,更关心产业整体发展目标,而非利润最大化的单一目标。国企更受银行和金融资本的青睐,能获得更多长期融资,即“耐心资本”。国企也保持着长期雇佣的人事制度,人员梯队较为稳定。国企更易通过体制内网络,协调更广泛的组织网络,如上下游企业、科研机构,甚至行政部门。
反观民企,追求利润最大化,甚至短期利润最大化,是大多数民企的决策目标,且中国民企以中小规模为主。因此,民企更能充分发挥“船小好调头”的优势,更好地创新试错,更迅速地适应市场,发挥价格机制的激励、引导优势。然而,当前多数民企依然面临融资难、融资贵的困境。无论在规模还是持久性上,多数民企融资都很难与国企相比。市场化的雇佣制度,也使得民企的人员流动率更高。
澎湃新闻:中国不同所有制混合的产业体系能为技术创新提供何种制度优势?您的研究成果有何现实意义?
陈玮:论文从治理模式、金融关系、劳资关系、组织网络四方面,分析国企和民企所处的制度环境,如何塑造企业不同的创新优势。国有体制更有利于塑造企业追求长期目标、获得耐心资本、实现稳定的雇佣关系与组织网络的能力,因此国企在“长周期技术”产业创新方面更具优势;民营体制则更有利于塑造企业的市场反应与组织调整能力,因此民企在“短周期技术”产业创新方面更具优势。
在中国产业体系中,国企与民企互补,双方基于各自优势,展开多样的产业布局,追求不同领域的技术创新,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制度优势。多样且互补的产业创新体系,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,也能为广大后发展国家提供创新发展的新路径。中国的体制特色与发展经验表明,在培育技术创新方面,所有制混合的产业体系能发挥不同的制度优势,全面推动前沿技术的突破。
长、短周期技术产业对创新能力的要求与挑战
澎湃新闻:从长周期与短周期技术产业对创新能力的需求看,国企与民企各自具有怎样的制度优势?
陈玮:国企在长周期技术产业的创新更有优势。初创时期,长周期技术产业准入壁垒高、投资大、前期收益低、技术积累时间长,这就需要大量、长期的资本投入和稳定的人才梯队。国企能有效利用政府在整合资源、提供资金方面的优势,持续为长周期技术产业注入耐心资本、培养技术人才、建立稳定的产业合作网络,克服初创时期的挑战。
因此,中国发展长周期技术产业离不开国企的助力。比如,中国商飞承担着研制大飞机的战略任务。作为国企,商飞不仅能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,还能通过国有资本体系获得大量融资。因此,商飞能制定长达10年的人才发展目标,并实施各类人才培养计划。同时,依靠国企为主体的国有航空工业体系,商飞能拥有相对稳定的“政-产-学-研”网络,持续研发技术。
短周期技术产业变化快,允许企业跳过知识积累阶段。因此,拥有资本、人才的初创企业,能很快进入市场,与现有企业平等竞争。此外,由于市场参与者拥有最新技术,配有最新设备,因此享有极大的“后发优势”。不过,随着具备尖端技术的新参与者持续出现,先发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时刻受到威胁。因此,先发企业必须通过不断更新技术、重组组织内部结构、调整产业合作网络,快速灵活地应对变化。
民企成长于“资源稀缺”的制度环境中,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和融资约束。这样的制度环境塑造了民企对市场的敏锐嗅觉、灵活的组织调整能力,这也是短周期技术产业所需的创新能力。比如,无人机龙头企业大疆早期进入市场时,也面临了资源有限、人才短缺、融资困难等民企的共同困境。如何缓解资金压力,如何在市场捕捉盈利机会,如何让企业快速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,就成为大疆等民企的必修课。
澎湃新闻:国企与民企所处的制度环境差异,塑造了企业不同的创新能力,应如何满足不同产业的创新要求?还存在哪些问题?
陈玮:一方面,国企所处的制度环境,塑造了企业追求长期目标、持续投入资本,以及长期培养技术人才的能力。这正是高度依赖既有知识、需要长期知识积累的“长周期技术”产业创新所需的必备能力。这类产业对创新企业的进入门槛要求较高,国企所处的制度环境,更能塑造进入产业所需的能力。另一方面,民企所处的制度环境,塑造了企业紧跟市场、灵活调整组织的能力,恰好能满足技术更新速度快的“短周期技术”产业的创新要求。
不过,没有任何一种制度环境是完美的。国企所处的制度环境,虽然能为其带来耐心资本和技术积累的有利条件,但也“软化了”国企的预算约束。在这一制度环境下,国企会面临决策滞后于市场变化、组织与网络僵化的问题。民企所处的制度环境虽然灵活,但由于融资不足,难以长期专注于溢出效应更大的创新活动。
不过,在实践中也看到,虽然国企更能提供技术创新需要的耐心资本,但国企也面临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考核要求。因此,国企投资对投资风险的容忍度并未达到社会预期,投资比较谨慎。特别是对于早期投资来说,由于技术创新风险高,创业成功率低,需要更为健全的退出机制,这成为国有资本投资的痛点。
因此,我们应充分鼓励、维持“多元的制度环境”,进行技术创新的自主选择。让需要耐心培育成长的创新,得到国企制度环境的支持,也让市场变化激发的创新,找到适合的民企制度环境。国企能提供耐心资本、长期雇佣和稳定的协作网络,民企能塑造企业的市场敏锐度和灵活的组织调整能力,两种制度环境在技术创新中相互补充结合。如此一来,就能最大程度发挥“中国体制”的独特优势。
澎湃新闻:适配的制度环境是企业技术创新成功的基础,国有与民营体制之间,如何根据产业技术特性形成相对合理有效的产业布局?
陈玮:处于“多元的制度环境”中,参与长周期技术产业的企业大部分是国企。一旦克服初创阶段和市场准入的挑战,长周期技术特征使得国企较易维持先发的相对优势。另一方面,短周期技术产业的企业,获得新技术及市场准入更容易,然而进入市场后,民企必须保持灵活性与适应性优势,否则可能因激烈竞争而失败。
当一个产业属于典型的长周期技术时,适合类似国企所处的制度环境。比如大飞机产业,研制时间需要20年,投入成本巨大,民企通常望而却步。不过,一旦进入该行业,即将面临的技术冲击和挑战者都相对较少。因此,中国的大飞机产业基本以商飞为主制造商,并启用整个国有航空体系为供应商。现实中,很多产业的技术周期介于大飞机和无人机之间。因此,在很多产业中,国企与民企并存,各占一定比例。
要想根据“产业技术特性”,形成合理有效的产业布局,既涉及政府职责,也关乎企业选择。一方面,政府要有长远眼光,维持一个多元的制度环境,通过法规指令的规制或优惠分配的带动,引导企业做出匹配其技术特性的选择。另一方面,企业也需勇于探索,发挥产业优势,做出明智选择,这是一个“试错-演化”的过程。
同时,为了推动科技创新发展,国企需要更多耐心资本,民企需要更多创新空间。创新制度是一个“生态系统”,中国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有两方面优势。一是政府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、国企体系,能为基础性的、需要技术积累的产业技术创新,提供耐心资本、风险资本。二是中国较大的应用市场,能支撑各类技术路线不断试错、竞争,通过优胜劣汰筛选出最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产品。
政府与市场哪个对技术创新更重要
澎湃新闻:您在学术研究中还存在哪些困惑?认为目前学术研究环境如何?应如何解决面临的问题?
陈玮:在我的研究领域中,关于“政府与市场哪个对技术创新更重要”的讨论较多。具体来说,目前的主要困惑在于,“集中”机制还是“分散”机制更有利于创新。不同机制都有最佳的适用条件,我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。
中国的学术研究正走向“集中式创新”,具体表现是资源和机会向少数的、知名的团队集中。对一些需要在短期内攻克的研究课题,“集中式创新”具有特定优势。但是,如果要培育长期的、有活力的创新生态,也需要广泛的、分散的科研环境。我们应该追求一种多元的、兼容并蓄的科研环境。
此外,目前学术研究的学科性、专业性更强,但也存在学科壁垒增强的趋势,导致学科之间缺乏交流。比如,我所研究的技术创新议题,也受到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管理学领域的关注。我采用的是比较政治、技术经济的相关理论,未来希望在多个学科共同关心的议题上,形成跨学科交流的环境。
澎湃新闻:2025年,您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有哪些未来规划,计划重点研究哪些课题?
陈玮:我是以比较视角探讨政府与市场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,未来仍将延续这一视角。一方面,比较全球不同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,为中国的技术创新提供借鉴。计划重点研究的是,在当下新能源、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创新中,自由市场经济、协调市场经济的得失。另一方面,探索中国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机制建设,凝练中国创新体系的特色,为技术创新的政治经济理论提供新的视角。计划重点研究两方面。一是中国的政府引导基金,如何在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中,提供耐心资本、共担风险。二是如何构建有效的合作机制,有机结合政府(国企)和市场(民企)优势,打通从技术创新到技术商业化过程中的堵点。
免责声明: 本文来自梵星网创作者,不代表梵星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本网页内容均来自网络采集,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司联系。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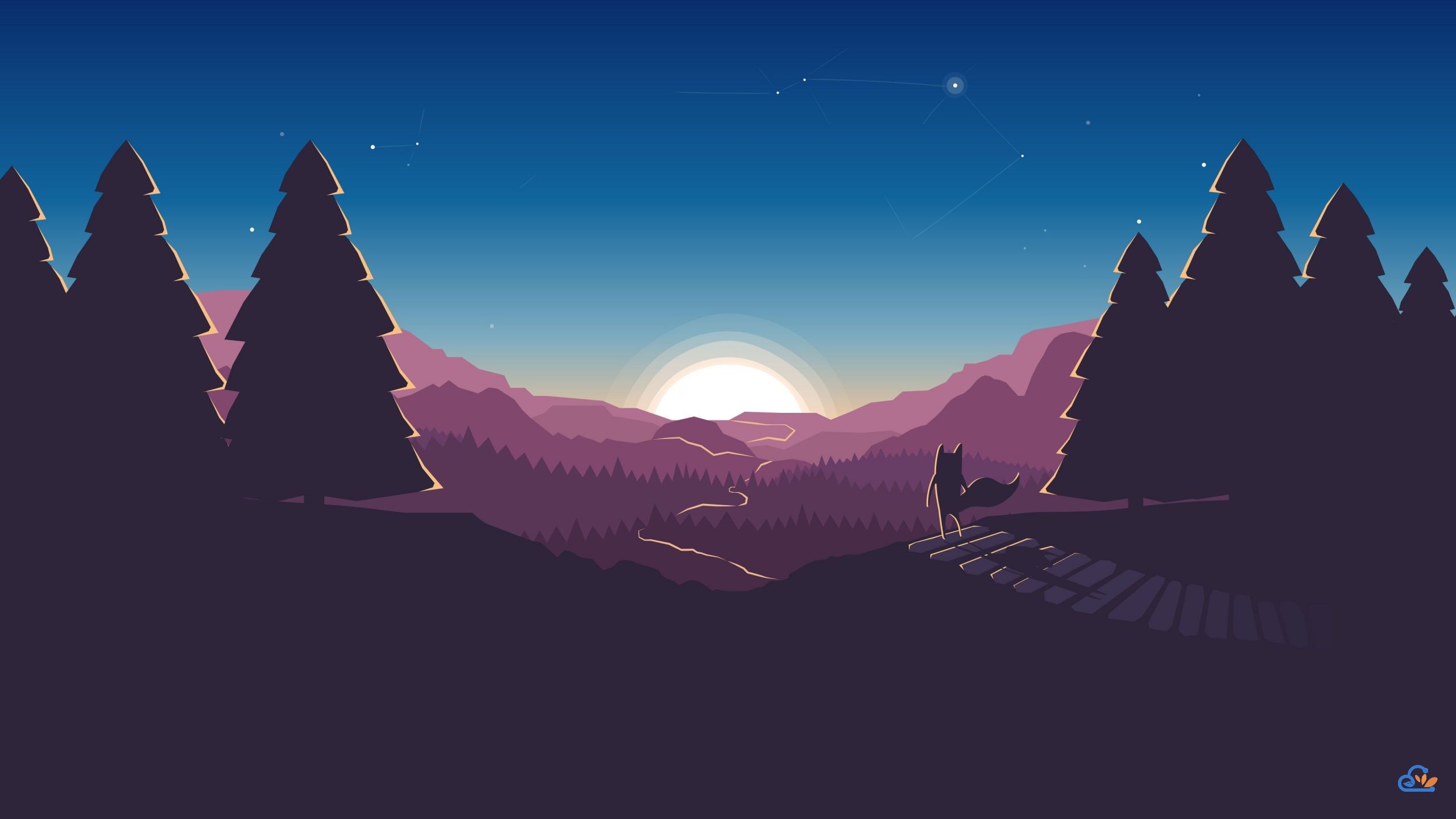

暂无评论内容